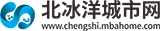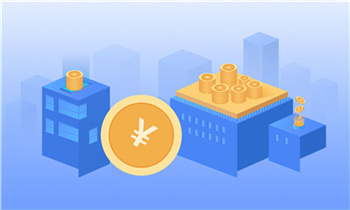本文已获授权
来源:一席(ID:yixiclub)
 【资料图】
【资料图】
李杰,iSTART儿童艺术节策展人。
我一年可能要跟一千个这样的小朋友合作展览,所以我每天都在被洗礼,都在刷新我对儿童的认识。
童年美术馆
大家好,我是李杰,是一位在美术馆工作的策展人。
可能大家会有一些关于美术馆的想象,但是在我工作的十年里,我发现现在的美术馆和博物馆,对儿童和家庭来说并不是那么友好。
比如说我听到过很多家庭的抱怨:美术馆和博物馆的灯光太暗、作品的信息太少或是导览员只是自顾自地在讲,孩子们只能跟在后面。
今天就讲一讲我们美术馆的一个项目,叫作iSTART。
这是A4美术馆的外景,在成都的麓湖湖畔。
2008年,汶川遭遇了特大的地震,美术馆的空间也受到了不小的破坏,馆长孙莉女士带着团队去了灾区。
从 那时起,我觉得成都这个城市在基因上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因为更多的人开始不只是关心自己的生活,也开始关心他者。
进入灾区后,我们团队有一种挫败感,因为面对那么极端的天灾现场,我们很难想象应该怎么做。我们只能通过艺术课堂的方式,去帮助在地震当中失去亲人的孩子们做心理康复。
▲ 2008年6月,四川映秀灾区·艺术课堂
在那之后,孩子们就进入到了我们日常的工作领域当中,A4美术馆从一个单纯的当代艺术中心,开始向更多的公共教育机构转型。
到了2011年的时候,我们策划了第一场真正为了孩子的展览,这个展览的面积只有一百平米。
我们跟植物学家、景观设计师、大学生和社区的孩子们一起合作,孩子们每个星期都会来几次美术馆,因为他们要去看自己播种的植物在美术馆里生长得怎么样。
2013年有一个小插曲,也改变了我们如何去为孩子们创造一个空间的想法。在那次展览中,有168个小朋友画了很多漂亮的画。我们当时设计了一个空间,专门去展示他们的绘画。
但是孩子们觉得这个空间很小,他们希望独占这个空间,不希望大人进去。所以我们就把入口设计为只有一米高,禁止所有的成人进入。于是家长就像沙漠里的獴鼬一样,在圆洞里窥视他们的孩子。
这些圆盘都是用鱼线挂在天花板上的,很不幸的是,孩子们用了一天的时间,就把上百个圆盘都拽到了地上,在地上滚来滚去。
我的同事说这是一个设计事故,我们应该把这个门关上,让家长和孩子们在外面看就行了,实在不行给他们在一米以下再多开几个孔,让孩子们钻着头往里看。
我始终觉得有些不对。我们就昼夜奋战把画挂上去了,最后做了一个决定——我们在地面上增加了一百多个圆盘,孩子们还是可以在里面畅游。
很神奇的是,再也没有大批量的圆盘被孩子们拽下来。更小的孩子在里面滚着圆盘,享受他们独占空间的快乐;而更大一点的孩子会非常仔细地观看每一幅画作。
在博物馆和美术馆里有非常多的“禁止触摸”“禁止入内”的空间提示,从心理上,它让更多人远离了所谓的文化和艺术。
这个展览过后,我们开始去研究孩子们的行为,并且让他们在适合的空间和项目中去感受艺术。
我们走访了很多儿童博物馆后发现,他们采用了让孩子们去亲近这些艺术的方式,让孩子们从一个观察者向一个创造者和行动者迈近。
这个项目来自另外一位艺术家,他叫黄淋。他在2017年的时候,做了这样一个作品。这件艺术品又一次改变了孩子和艺术家的互动方式。
这个艺术家所有的东西都来自于生活日常——那些做家具时会用到的一些小的零件和废弃的零件。这些零件最后就被这个艺术家拼装起来。
但是他的游戏规则是,所有现场的观众,特别是小朋友,都有权利去改装他的作品。他说出这个话后,我们背后一身冷汗,因为这等同于这个作品每天都要被重建一次。
有些孩子在这么一个小小的展厅里待上四个小时,他们的家长不停地对他们说,家里不是有乐高吗?为什么在这玩这个?但是孩子就是不走。
我们开始研究童年的历史,我们发现人类实际上处于长期忽视儿童的状态,甚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类对于儿童是很惧怕的。因为孩子在没有成人之前是社会的不安分分子。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在大部分的童年历史中,关于儿童的记载是苦涩的——儿童有很高的死亡率,很低的教育率,家长实际上是把孩子变成他们自己想塑造的成人。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做了“童年疗养院”。我们把整个展厅设计成了不同的科室,每个艺术家为孩子们做了不同的房间,每一个房间代表他们的童年以及他们理解的童年。
这个展览中有一个特别的设计。因为我们无法阻止孩子们在展厅里面奔跑,所以我们跟设计师徐浪讨论,应该想出一种方法,能够改变孩子们在展厅里的状态,让他们更自由一些。
于是我们把所有展厅的墙面都改造成距离地面只有一米三的距离,孩子们可以在墙面下自由地穿行,但是成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他们必须要弯身通过。
有一次,我在导览过程当中听到了“嘣”的一声,一个爸爸狠狠地撞在了展墙上,明显是他刚才在看手机,忘了看前面的几道提示。他非常气愤,用拳头砸墙,然后他那可能还不足四岁的孩子拉着他的裤脚在安慰他。
我们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突然明白了这个童年疗养院的意义,有些时候这不是对孩子的疗愈,而是对成人的疗愈。因为在这个时候,这个爸爸更像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
这个小男孩叫吴联成。当时他和团队要一起制作一个独立动画。
吴联成是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从46个小朋友中脱颖而出,成为短片导演和团队的领导者。
但是他把剩下的小朋友都作为他的副导演。他带着这个平均年龄只有12岁的团队整整工作了半年。
从原画到设计到所有的分镜头,再到最后的电影原声都由他们自己完成。最后我们只找了两个大学生帮助他们剪辑,和他们一起完成了这部八分钟的动画。在这之前他们从来没有做过类似的事情。
那时我正在国外做美术馆的调研,有时差,所以吴导偷偷地用爸爸妈妈的微信跟我讨论剧本。
我们经常会接到几十条甚至近百条的59秒的留言,都来自于吴导非常生动的,像评书一般的剧本故事,每一天的剧本都有变化。
我一年可能要跟一千个这样的小朋友合作做展览,所以每天都在刷新我对儿童的认识。
这是吴导和团队在讨论剧本。
这个动画的内容是关于两个屌丝如何拯救了世界。他们有一个人类回收计划,这个计划激怒了外星人,然后外星人企图要侵占地球,毁灭人类,他们要通过练级打怪的方式,最后去战胜这个外星人。
这是他们自己画的原画。
中间有非常多精彩的故事,情节堪比《三体》。但是因为情节太过复杂,最后这个片子可能只完成了不到百分之二十的剧情。
因为吴联成的口才和领导力,他现在已经是学校的大队长,而且他也是他们学校音乐课的选修课老师。因为他们的老师在一年后表示已经无法去教这个孩子了,这个孩子的自主学习能力已经非常强了。
▲ 《先知纪元》展览现场和放映
在2018年,另外一个项目是一部60分钟的电影。这个项目是由纪录片导演杨然、毛姝老师还有一个小朋友合作的,这个小朋友叫冯可人,13岁。
当年展览的主题是根据刘慈欣的小说《超新星纪元》去改编的,这个小说讲的是人类遭受了一次宇宙射线,所有13岁以上的成人都消失了,然后孩子们会去接管地球。
我们把这个命题交给了上千名儿童,让他们来想。
冯可人小朋友的方案是和纪录片导演一起完成一次召集。她会去四个志愿者的家庭,去告诉这些父母,“你的孩子必须要了解你终将离开他们,你怎么给他们解释你现在的工作,你要跟他们共同做一件事情,让他们学会独立成长。”
这个影片中有一个妈妈,她是一名老师。由于工作的原因,她把大量的时间都奉献给了学生,所以她跟自己的孩子之间反而缺少了很多交流。
当孩子14岁的时候,她和她的孩子产生了很大的隔阂。所以当冯可人问这个妈妈“如果你离开了这个世界,你的孩子会怎么样”的时候,这个妈妈不假思索地说,我觉得我的孩子可能会很开心。
而当冯可人去问这个孩子的时候,她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答案。这个孩子几乎无法接受这个现实,面对镜头久久不愿回答。甚至到了最后,她都不愿意相信这个有可能会发生。
最后这个孩子和她的妈妈十四年来第一次面对面聊这个问题。他们互相哭泣,拥抱在一起。短短几十分钟的谈话,帮助他们打开了十几年的心结。
这个影片的最后拍摄了两个孩子,他们是一对兄妹,是所有被访者里年纪最小的。这个哥哥很内向,一直不愿意直面镜头和问题。
他们最后要在一起做一件衣服,来体验妈妈的设计师工作。
这个哥哥正在做一件送给妹妹的衣服,但是他一直不停地想在这件衣服上安装LED灯。当冯可人问他,你为什么做这件事的时候,小朋友对着镜头很腼腆地说:“因为妹妹喜欢,妹妹认为这是她的灯塔。”
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五六岁的孩子能够理解作为家长应该做什么,或者是作为一个成人应该担当什么。但是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镜头理解了,这个孩子一直不说话,他并不是不明白,而是在用他的方式表达。因为他知道如果他的爸爸妈妈不在这个世界上,他就是妹妹唯一的家人,他就是这个家的一家之主。
我在2017年的时候得到一本其貌不扬的小本子,这个本子来自三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他们从九岁开始花了三年的时间,秘密地通过传递的方式,在本子上写满奇怪的字。
这个本子是带锁的,所以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本子是干什么的,包括他们的父母,他们的老师。最后他们把本子交给他们信任的老师,这个老师也很信任我,因为她是我的太太,她把这本带锁的小本子给我看了。
我看后很震惊,因为这三个小女孩要干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她们要建立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名字叫作GAGA国。
▲ GAGA国创始人赵越、刘星源、苏天奕
最后我们通过美术馆,招募到150位小朋友成为GAGA国的公民。
这是她们的展厅。
在这个“国家”里,有她们关于这个世界的想象。
这是她们设计的国旗,旁边是大使馆入口的接待处。
这个国旗上面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信息,比如她们创造了一种新的语言。
我问她们,你们都做了这么酷的事情,为什么还要那么费劲地去创造语言呢?她们告诉我,因为违法呀。她们知道不能在一个国家建立另外一个国家,所以要做一套成人看不懂的语言。
这是GAGA国的“宪法”,她们在“宪法”的第一条写了一句话,意思是:GAGA国是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共和国。我一想觉得不对,又是君主立宪制,又是共和国,这不是矛盾吗?
她们非常自信地告诉我:“英国也是君主立宪制,但是那个女王就是一个吉祥物,跟我们GAGA国的鸭子公主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真正的国体实际上是一个共和国,叫宇宙共和国。”
GAGA国的阶层非常有趣,最高等级的国民是叫花子,最低等级的是总统。
真正的大使馆是要运作的。她们是大使馆的官员,级别比我高,我无法安排她们的工作,她们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所以在现场有非常多的观众每天都在等她们发护照本。
她们还设计了八道问题,第一道问题就是关于GAGA国的国旗:“请问国旗上面的蛋是鸡蛋还是鸭蛋?”
对于儿童来说,这些根本不是问题,但是一些不认真看展的成人,大部分问题都答不上来。所以他们就偷偷地让我们递答案,帮他们获得GAGA国的护照。
GAGA国有非常严谨的地理系统。
以及他们的生理结构。
还有拼音表,就是这个国家的语言系统。
这是GAGA国的货币,可以发现他们通货膨胀还是很厉害的。
这是GAGA国的宇航飞船,因为GAGA国是飞到地球来的,为此她们做了一个巨大的装置。
还有像《圣经》一样的神话和历史。
甚至还有璀璨的艺术品。这张画的是,有一个长得像鸡爪子的外星民族的GAGA国的敌人,驱赶了他们,侵略了他们的国土,最后他们整体逃到了地球,然后受到了地球文明的影响。
所以才会出现《蒙娜嘎莎》这幅名画。
她们在某个角落画了一张霍嘎尔学校,是GAGA国的学校。学校的外立面是没有窗户的墙,墙上都是装饰物,但是墙旁边有一个跳板,这是跳楼台,孩子们是通过跳楼的方式毕业的。
其实在她们画这幅画前不久,国内出现了一些学生自杀的情况。我们发现很多时候学校没有进行太多的心理干预,而孩子们把这些信息留存到了意识当中,他们不知道如何去疏解,就正好通过这个项目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在霍嘎尔学校,毕业跳楼不会死,但是你会掉到一个清澈的水里,这个水有一种特殊的功效,跳进水里之后,你所有对学校和教育的抱怨和负能量,都会被这个水吸收掉。当你毕业后面对下一段人生的时候会变得非常轻松快乐。
这个学校的下面像一座巨大的冰川,更大的一些建筑体都是实验室,在这些实验室里面可以分类地把这些负能量吸收,通过机器转化成能源。她们告诉我,这个能源是帮助这个学校继续招生的。
我听过这么多精彩的小说反思和批评今天教育体制,但我从没有看到过这么精彩和有锐度的言论。
到了今年,我们的主题就回到了学校。iSTART今年给孩子们开放的主题叫作“再见学校,你好学校”。
今年我要下岗了,因为我需要把策展人的工作也交给孩子们。所以我们就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从幼儿园到高中,去学校里做公开课和工作坊。
这是在成都实验小学,孩子们通过回答我们的问卷参与到这个项目中来,然后自己提方案,像写论文和策划书一样,完成他们对于展览的想象。
他们对这件事充满热情,因为这是他们最想做的事情。
这些是来自各个学校的问卷。当孩子们无法用语言去回答我们的问题或是他们自己写的问题时,他们就用图画来完成。
他们需要表达的空间,但是我们以前没有给他们那么多出口。
我们还做了数据分析,我们发现特别是小学生,他们不太喜欢教室,他们喜欢操场;他们也不喜欢厕所,不太希望有太多的作业,但是他们希望有更多的像图书馆这样的空间,可以让他们自由地学习。
当面对这些具体问题的时候,他们不像成年人那样在抱怨,而是会想出很多的方法。
比如针对厕所的问题,孩子们做了一个改造厕所的方案。
以及他们对于新的学校的计划。
还有更多的孩子把他们的方案投递给了美术馆,希望在美术馆里来呈现。这些是来自初中的孩子们,他们对于未来学校的想象就更加细致和抽象。
还有孩子们的答辩,就像大学生和研究生一样,他们通过分享各自不同的方案去了解彼此,去找到共同点。
在今年八月份,iSTART第五周年的时候,他们还要重新组队来呈现他们在美术馆里面的新的学校。
我们今年会开辟更多的分展场,更多社区学校向美术馆开放了。有些学校甚至把这些项目变成了他们的年度项目,可能到每年的八月到九月,会有更多的学校在学校里建立他们的美术馆和博物馆,在学校里举办他们的艺术节。
▲ 成都红星幼儿园iSTART分展场
以前都是老师们提出想法让学生来完成作业,现在变成了让孩子们来想象,让孩子们来参与。会有更多的像冯可人、吴联成、GAGA国的创始人这样的小朋友,开始成为这个项目的主角。
这个项目也变成了A4美术馆十一年历程当中最受公众欢迎的项目,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2016年停办了一次过后遭到了很多市民的投诉。
这是去年iSTART开幕的时候。
我希望通过这次演讲,能够让更多的人打开行业壁垒,打开空间,让更多的孩子去参与,去发声,因为他们不单只是模仿者和学习者,他们其实是创造者和行动者。
谢谢大家。
本文授权转载自一席,儿童设计大数据推荐发布
我们的小目标 :
2年内,发布1000个儿童设计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