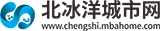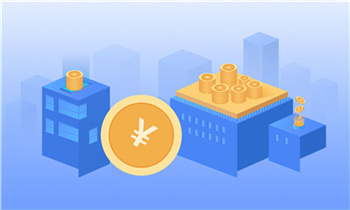日本政府召开的最新一次内阁会议,决定任命经济学家、东京大学教授植田和男为日本央行行长。作为“二战”后首位学者出身的日本央行掌门人,现年71岁的植田和男很有可能在接下来的5年任期中将日本货币政策导向正常化轨道,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YCC)的走向。
 (相关资料图)
(相关资料图)
日本央行自上个世纪90年代末就推行量化宽松政策(QE),及至黑田东彦出任行长时,又加码推出了包含YCC在内的量化与质化宽松政策(QQE)。起初日本央行确定的YCC变动区间即“利率走廊”为-0.1%至0.1%之间,但其实仅关注的是利率走廊上限,即当10年国债收益率上行至0.1%时央行便下场采购国债;针对经济增速和通胀均出现上行趋势,2018年7月,日本央行将收益率波动幅度扩大至-0.2%至0.2%之间;2021年3月,日本央行又将区间扩大至-0.25%至0.25%之间。至2022年12月,日本央行再次扩大YCC区间至-0.5%至0.5%。YCC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压低长期利率来降低央行购债成本,从而为市场提供充分的流动性,进而刺激经济增长。
一般而言,在央行宣布或者已经实施收益率曲线控制的情景下,市场会获得较为强烈的信号效应,即货币政策在更长时间内持续宽松,利率也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维持更低水平,由此在很大程度上稳定市场对中长期利率的预期,包括居民消费可能会因为借贷成本和储蓄收益的下降而增加,企业也可能在低利率的刺激下增加投资,政府融资活动也可能增多并增加支出,最终对经济增长以及物价水平形成促进与拉升之力。
反观日本YCC的行进过程,启动后的一段时间的确产生出了一些积极效果,比如物价水平脱离了负增长并持续表现为正,出口获得了明显改善,贸易顺差持续了多年,就业与经济增长也获得了不少改观等,只是任何最初看上去不错的政策都可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成为对现实的禁锢与羁绊。
其一,日本并没有随着YCC的延续而摆脱通货紧缩。YCC的最主要目标是推升通胀预期,但近20年来日本年均CPI仅0.1%,即便是YCC持续运行的5年时间内,日本国内CPI年均涨幅也只有0.68%,不仅远离央行的管理目标,而且期间还有三年CPI增长为负。虽然由于俄乌冲突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行,日本国内的通货膨胀率去年出现明显回升,但是此时的通胀搭配YCC带来的是日元持续贬值,而非内在需求的真实扩张。
其二,YCC引起的日元贬值超预期,同时贸易收支随日元贬值出现恶化。YCC不仅会抑制长端收益率,也会隐射并下拉短期货币利率,日元在国际资本眼中失去吸引力,尤其是在美欧央行大幅加息背景下,日元的贬值风险被加速放大,资本纷纷逃离日本。按道理,日元贬值有利于日本出口,但由于能源价格上涨的强烈对冲,日本出口却远远逊于进口,最终日本经常项目顺差在去年创下八年来的最低水平,出口对经济的贡献为-0.6%,若算上资本项目的逆差,去年日本贸易逆差创下了自1979年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新高。
其三,金融市场价格发现功能因YCC的延续而偏废。中央银行基于收益率曲线控制的购债操作,客观上形成了央行对国债收益率进行“兜底”的市场预期,市场也紧盯央行购债行为展开交易,呈现出“市场不看市场看中央银行”的行为特征,最终日本央行成为了10年期国债的最大持有主体,持有规模近70%。另外,YCC人为压低日本国债收益率,扭曲了长短期国债收益曲线,虚高的价格也挤出了众多国际投资者,10年期国债的二级市场交易量枯竭,甚至一度出现“零成交”,国债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遭遇严重压制与扭曲。
最后,YCC形成对央行采购的倒逼进而损害央行独立性。在锚定“利率走廊”上限的前提下,随着收益率的不断“破位”,日本央行不断下场救急,某些情况下央行还必须加大购买力度,而且由于政府债务水平过高,财政部也存在持续面向央行加压的倾向,并要求央行尽可将收益率曲线控制维持更长时间,而基于对债务风险的担忧,日本央行也会被动承诺与无奈隐忍,但同时又必然损害自身独立性。另外,不断地“扩表”已使日本央行遭受的账面损失达到8.8万亿日元,占GDP的1.6%,央行接下来可以支配的货币政策增量工具受到抑制。
进一步观察发现,去年日本物价涨幅达到2.3%,而来自日本总务省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日本国内CPI继续高开高打,月度同比劲升4.2%,为1981年9月以来的最快增速,虽然2月和3月物价涨幅连续回落,但依然超出央行控制的目标水平。另外,去年日本人均工资月均增长2.1%,为近31年来的最大涨幅,且连续2年增长,今年还会继续上涨,日本国内存在着工资-物价螺旋。对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明确表示,日本通胀具有上行风险,建议日本央行调整政策,提高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的灵活性。
还有一个非常严峻的事实是,基于本区域通胀并未实质性减弱的事实,欧美等主要经济体中央银行今年还要继续加息,如果日本央行依旧按兵不动,日债与美债收益率“剪刀差”会进一步拉大,资本从日本撤离的脚步也会再度提速,日元贬值的压力势必继续提升,并由此导致的输入型通胀将进一步恶化。因此,正如当初是基于通货紧缩的倒逼不得已推出了YCC,如今面对通胀可能失控的趋势,日本央行也极有可能被迫调整YCC。
按照植田和男的说法,“长期利率控制是一种不适合微调的机制,若利率上限小幅上调,市场对后续加息的预期可能会进一步导致大量政府债券抛售”,因此,就任央行行长后,植田和男不会在YCC的调整上采取渐进方式,而会选择一次性退出,同时在量化宽松工具的调整次序上,植田和男会选择放弃YCC-停止负利率-退出QE的“倒序”步骤,也就是先“价”后“量”的节奏。
无疑,选择一次性退出YCC势必会令日债收益率急剧上升,市场由此非常担心是否会酿成日债违约风险。的确,目前日本政府债务占比超过了260%,为发达国家中的最高水平,但根据IMF的测算,日本政府债务的平均利率为0.62%,利息支出仅为GDP的1.6%,显著低于美欧等主要国家水平,而且日本政府债务平均期限为8年,国债收益率上升短期只影响新增债务的融资成本,对存量债务成本的直接传导非常有限,何况通胀上升阶段,伴随着名义GDP增速的回升,财政收入增速通常上升更多,可以抵消付息成本压力,因此总体判断,直接退出YCC短期内令日本政府债务不可持续的风险较小。
但相比于对国内债务成本提升难以构成危机压力,未来日本央行对YCC采取的激进手法针对全球金融市场的溢出风险在短期内可能要大得多。过去十年,在超宽松货币政策以及YCC政策下,为了获得更高收益率,日本投资者将价值3.4万亿美元的日本国内资金投资于海外市场,既成为了美国政府债券最大外国持有者,还在全球股票市场投入了54.1万亿日元,持有的股票相当于美国、荷兰、新加坡和英国股票总市值的1%-2%,而紧跟YCC退出的脚步,日元加速升值,投资者的押注风险偏好上升,由此导致更多资本回流至日本。
根据日本财务省的最新报告,去年仅日本投资者减持的海外固定收益证券达23.8万亿日元,为过去27年来的最高水平,主要原因就是对日本央行将转向货币政策正常化的猜测推动了日本国债收益率的上升,提升了日本国债对投资者的吸引力,这种状态在YCC退出趋势非常明朗的背景下是否会扩大到市场更广的层面,从而令非日债金融品种面临更大的抛压或者引致全球金融市场流动性压力的增升就值得警惕。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
(文章来源:国际金融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