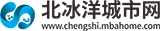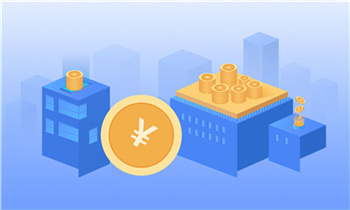“你呢,你为什么来这儿?”
 【资料图】
【资料图】
我正盯着湖面上几张纸发愣,无比确信数秒前它们还是戏水的鸟儿。头忽然很痛,我晃晃脑袋看向四周。乌云掩住半边天,湖畔是灰蒙蒙一片树林,脚底的落叶尚且湿软。我想,这大概是八年前那个秋日的黄昏。
“这是哪里?”我明知故问。他像是没有听见,我这才发现他也盯着那几张纸。等它们漂近,我看见上面写满了字。正伸手,听到一声很轻的叹息。
我看不真切,觉得他看我的眼神近乎哀怨:“是我写的——你已经忘记了 ?这里是柳湖。”
我一时不知如何回应,收手假装拨弄脚边的草。拔到第五根时我告诉他,我在写一篇小说。他看上去高兴了一点,开始和我一起拔,说我小时候就喜欢听他的故事,那时才这么高一点。也许是抬头比划时又看见水面的稿纸,他突然问我:“这么说,你找到‘季鸟儿’了?”
我看向别处,鼻头有些酸:“我写了很多,自从、自从你……”
“这样不好……”他打断我。我不确定他说的是什么,但他摇摇头,不再说话。
他想了很久, 直到我们面前没有可拔的草。这时什么声音越来越大,我抬头看见稿纸漫天飞舞,像无数只鸟儿在扑棱翅膀。风很大,天边隐隐闪烁了几下。
“雨要来了,”他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开始活动四肢。我恰好抓住一张纸,试图辨认上面的字。等我反应过来慌忙站起时,湖水已漫过他的腰际。他回头,露出记忆中温和的笑容,尽管脸色有点些苍白:“我必须走了。”
我知道救不了他,他是那么坚定,就像八年前那样。站在这里让我难受,我喘不上气,想要跑开却无论如何也挪不开一步。雨水落在湖面激起水花,皱巴巴的稿纸漂过他没入水面的位置,我再也看不见他。隐约中,一条银色的大鱼从稿纸下游过。
第二天我从床上醒来时,还在想那条银色的大鱼,一定是因为窗外淅淅沥沥的雨,我的思绪积满水,任由大鱼在房间里上下游动。半掩的窗帘外透进淡淡日光,斑驳几点映在墙上,倒像池底的光影。大鱼、大鱼,你想告诉我什么?大鱼只是徘徊,每次回头都摆动巨大的尾鳍,好像搅动一汪星尘。我想我见过它,不止一次地。 我昏昏沉沉快要睡去,大鱼变得急促,左右摆动着在房间中央停留。它像一加支箭,射向我的桌面,消失了。我忽而发现桌上横七竖八摆着白色的东西,像死去的鸟。我似乎闻到空气中弥漫的腐臭气味,看到粘稠的褐色血液谪落,浸透凌乱的羽翼。我猛地扑向桌子想将它们清理,却发现攥在手中的不过是几张稿纸。十一点三十五分,亮起的手机屏幕上是十几条未读消息。头很痛,我摸索着坐下,一手扶住额头倚在靠背上。
“雨生——你起了?怎么不开灯?”老妈推门,顺手打开灯“吃饭去。”
老妈看见满桌的纸,猜到今天是公布结果的日子,便问征文的结果,很兴奋地说起她获全国大奖的作文。
“没有人入围。”我打断她。
“你呢?”
“没有。“
“啊……”她的声音小下去,“没什么的。”
她还想说点别的,却只拍拍我的背。我耸耸肩表示无所谓,这本来是意料之中的事,我只是后悔熬夜。头像灌了稀泥,我晕乎乎坐下扒拉饭。
“迟余叔真的变成一条鱼了吗?”我抬头,顺手把一块西红柿夹到碗边。
老妈停下夹菜的筷子,嘴巴动了动保持在半张的姿态,愣了好一会儿才咧嘴笑笑,问我是不是看迟余的小说了。我没有接话,满脑子是昨晚的梦。
我记得小时候经常梦见柳湖的傍晚,晦暗的光线中树影连成一片,云是灰灰的,天边有一丝眩目的亮光,快下雨了。梦的开始我总是急急地寻找,拾起一张又一张散落的稿纸,想要拼凑出完整的故事。文字往往残缺,当大雨倾泻而下落入柳湖,我看见一条银色的大鱼游过。
梦在这里结束,八年前秋日黄昏发生的事早已模糊不清。它平淡得像一场柳湖的雨,带来片刻慌乱,随即汇入地下水流,成为少数人的记忆。即使是我,也在不久之后淡忘了那个黄昏的梦。直到昨天夜里,大鱼重新游入梦境。
也许是某种提示。这么想着,我问老妈知不知道“季鸟儿”。
老妈有些恍惚,像是已经盯着那盘菜很久了,难怪没有注意我的沉默。她眨眨眼看我,又望向我的房间:“你要写他?”
我不置可否,说迟余叔让我找她。
“什么时候?”
“昨天。”
她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继续吃菜。我撒了个谎,其实迟余叔早就告诉我他在找“季鸟儿”,让我也帮他留意。那时他还在楼下写作,大人们都不愿多说,让我少信他的话。我悄悄说给他听,他摸摸我的头,严肃地说不是所有人都能找到她。我不懂,但觉得这是一项荣耀,更加喜欢学他编故事。
“你叔叔……高中就说要给她写故事。”老妈忽然开口,看来在努力回想。
“那他写了吗?”
“写了好多,”老妈放下碗,“但他后来找不到那个‘季鸟儿’了,我们到处问,没有这个人。”
我起身帮着收拾碗筷:“我想看看迟余叔的房间。”
迟余的房间就在楼下,楼梯落了灰,门没有上锁方便我不时造访。以前他也给我留门,这样想着我推动嘎吱响的门。
潮湿的气息扑面而来,像陈旧的书。门边几块脱落的墙皮,带下我小时候涂画的痕迹。正对门是杂物和收起的小桌板。房间左侧,他的床用白被单罩好。书架上书本排列整齐,一半作参考,一版是装订的手稿。雨还在下,绵延而细密,雨声织成一张网,包裹房间。窗帘透光,染蓝小屋湿冷的空气,光线昏暗让我犯迷糊,盯着桌前陷入沉思。
迟余在桌前埋头书写。我经常找不到他,四处乱窜却发现他哪儿也没去,迟余就在这,写他的小说。像小时候那样,我坐在床沿看他。他写得很慢很慢,每写一点就要仰头望向天花板,嘴里念念有词。他会写很多版本,一页一页地念,问我怎么样。
“怎样了?”
“什么?”我一个激灵站起来,椅子是空的,屋里没有别人。
“你的小说。”
我看向声音的来源,是桌上的透明鱼缸,里面有一条银色的小鱼。我不确定鱼是否应该说话,它也许有自己的道理。
“落选了。”我有些不自在。看我故事的人不多,但谁都以为我能写出点名堂,于是所有人都落选后我成了“救世主”,被钉死在几页稿纸上。
鱼有些烦躁,抖动它漂亮的尾巴:“不是这个,是你的小说。” 我想了想,只能告诉它我一直在写。它点了点头,又像在摇头,绕着鱼缸转了几圈。
我走近,拿起桌面上一沓皱巴巴的稿纸翻找。这是迟余最后一个故事,他离开时就带在身上。那天风很大,有些纸还在水里,很多字迹都模糊了,剩下的部分难以判断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我依稀记得他对我提过,他要写的是一个会让所有人都震撼的故事……
“你来干什么?”鱼凑近缸壁,吐一个泡泡。
“我来看看……看能不能找到‘季鸟儿’的线索”
鱼左右晃动,似乎在仔细观察我:“你真的以为这是一个捉迷藏游戏?”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假装认真查看手稿。
“得了吧你,”鱼乐得一个摆尾跳出水面,溅起水花洒在我脸上,“谁一写不出东西就翻叔叔的手稿啊?你都快背下来了。”
我感到耳朵发烫,不知如何辩解,这时电话铃声响起替我解了围。
“我的救世主!你终于接电话了!你最好看看班群……”
“我知道。”
“额,那……出来逛逛?”
“嗯。”我转头看向鱼缸,里面没有水。我早该想到的,迟余不在,这里很久没有养鱼了。
“我写不下去了。”我瘫在长椅上,有气无力。
朋友站在一边看手机;“昨晚多久睡的?”
“很晚。”
“也不至于,”他打完字揣起手机,“小小一次比赛。”
不想接话,我抬头,透过枝叶间的缝隙看厚厚的积雨云。柳湖的夏总是心事重重,少有烈日当空的时候。满心热烈往往要化作阵阵雨水,才露出清澈的天空。这该是很适合写东西的地方,细雨带来丝丝清凉,也带来泥土的芬芳。
“还说写不了!你说!是不是在想怎么描写雨天?”朋友拍我一把。
我没有动,还是仰头望天:“我不明白。”
他笑了,挨着我坐下,也仰起头:“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吗?”
“什么?”
“一条鱼。”
我一下坐直,吓他一跳。他摆摆手继续说:“装在鱼缸里能看到什么?跳出去,我们才不是观赏鱼。”
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抖落一树雨滴淋在我们头上。朋友站起来:“走了,要下雨。”
和朋友道别后,我又回到长椅上坐下,琢磨他的话。他说得在理,我被困住了。鱼说得也在理,我不是现在才被困住的。我以为接下来鱼会出现在空中,摆着尾巴游来游去,再说点什么有道理的话,但它没有。于是我等了一会儿,回去了。
我不记得什么时候上的床,再醒来时被人牵着下楼梯,迷迷糊糊觉得自己变得很矮。进屋,那人支起小桌板,拉我坐下。
“我们讲故事好不好?”他的声音好像迟余。我怎么都看不清他的脸,便认定这是一个梦。
他没有等我回答,自顾自翻开手稿念起来。也许是太困,我撑头趴在桌上,听不清,看到迟余的嘴唇开开合合,像一条大鱼。迟余的故事并不讲给孩子,我已昏昏欲睡。
“雨生?雨生……”在陷入沉睡前,我听到他小声的呼唤。他一定缩回想拍我的手,然后把纸轻轻放在桌上,笑着摇摇头。
他唯一的听众是我,至少在我的记忆中。 他写人形的鬼怪,写忘记飞翔的鸟,写溺亡的鱼,写吃狼的羊……在这个写作还是件新事的小镇,没有人确定他书写着什么。老妈说他在外面当过老师,给杂志写过稿打过零工。我问他,他说没意思,什么有意思?他没有回答,只是写。
“既然如此,就写吧!”
我发现自己并没有睡着,而是被无边的黑暗包裹。这意味着我需要更多的思考,而不能假装发呆来改变局面。于是我故意大声说话,想要得到回应。回答我的是绝对的寂静,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有没有说过话。我被瘆得发慌,感到心里空出一大块,脑子也空空的,只想跑起来逃出这里。
我忽然看到一个浮动的光点,近了发现是鱼在游。它散发着梦幻的银色光芒,缓缓地游近。得救的感觉让眼眶一下子湿润了,但我清清嗓子,用轻松的语气对它说:“喂,你听到了吗?我说我要接着写。”
鱼不说话,自顾自游。我深吸一口气,声音更大:“我会找到‘季鸟儿’。”
“哼,你就笑吧!”我几乎是喊了出来,“我要写出让所有人都震撼的故事!”
我感到一阵莫名的释然,有些得意地看鱼加快了速度。等我反应过来它在冲向我的时候,已经没有跑的必要。我闭眼,没有预想中的冲击,却感到一阵眩晕,仿佛失去支撑,不受控制地向下沉去。
挣扎中我摆摆尾保持住平衡,摇晃脑袋发觉自己浮在空中,像是在迟余的房间。看来我变成鱼了。窗外雨声很小,天色还是阴沉。我一时想不起该干什么,就学着鱼的样子转圈,从空中观察房间。转到第三十七圈时,门打开了,来人径直走到桌前。我跟在他身后,看他铺开纸写起东西。房间那头,门再次打开,一个人影在床下躺下。我试图撞他引起注意,但他一动不动。
门开了又开,人影一个接一个走进房间,在书架前翻翻找找,靠墙思索,拿着稿纸踱步……桌椅吱呀响,纸张唰唰被翻动,最初的人影不为所动,拿笔写写停停。我被吵得晕头转向,觉得他们一会儿是迟余,一会儿是雨生,都重复着同样的动作,书写着不变的文字。
忽然,我发现床上的人影面貌变得清晰。他坐起来,瞪大眼睛望向我。我停下,不知所措地摆尾,他看起来和我一模一样。
“如果这是雨生,你是谁?”这声音像鱼,又像我,更像迟余在讲故事。
我感到自己变得沉重,抽离了鱼的躯体向下落去。半空中,鱼冲向书桌,床上的我猛地扑向桌子。鱼没入桌面的瞬间,无数个人影化成小鱼砸向地面,消失不见。撞击传来,我翻滚几圈停在房间中央。不知何时稿纸散落一地,纸面大大小小的水渍记录数不清的坠落。我想爬起来,发现自己还是一条鱼。房间恢复了寂静,雨声嘀嗒打着节拍,窗外传来雷声,大雨要来了。
思绪昏沉,我却为清醒所困扰扰,像一条漏网的鱼, 回不到大海又无处可去,等着被时间晾干水分变得干瘪枯燥。我说不上鱼和雨生有多大区别,我们在同一个故事里。现在我确信迟余变成了一条大鱼,如他笔下的故事。这未必是悲惨的命运。迟余的故事讲不完,于是他纵身一跃,游向远方。迟余已经不在了,而那带来梦幻的的银色大鱼,不过是困住雨生幻影。
窗外闪烁了一下,接着是轰隆的雷声。门后匆忙的脚步接近,门被一脚踹开。迟余背光站在门口,四处张望。
“你在地上干什么!”他急忙抓起我,门也没关就冲出去。我睁大眼,从指缝里看浓黑的云层翻涌,雨滴零星落下。他加快脚步一头扎进树林,松针的清香弥漫,我想他的目的地是柳湖。
拨开茂密的枝叶,视野终于开阔。他喘着气捧起我,笑起来:”来得刚好,下雨了!”我随他向上看,天边透出一线光亮,为参差的树木打上阴影,满天稿纸飞扬,挂在树梢,飘向湖面。这果然是梦,我们又回到了那个黄昏。
迟余张了张嘴,最终没有说话。他被迎面飘来的稿纸吸引,松手让我滑落湖中。冰冷的触感袭来,我看大雨倾泻而下,他浑身滴着水,举手接四散的稿纸。
闪电蜿蜒爬过天幕,惊雷炸响,一晃神我已站在岸边。风很凉,我直打寒颤。再看湖中,一条大鱼转了个圈,悠哉悠哉潜入深处。白色的影子掠过湖面,我抬头,成千上万的鸟儿飞向天边。云层破了个大洞,流出橙黄的光线,为雪白的羽翼染上金辉。
又一声雷响,雨水哗哗砸向窗户。我睁开眼,就这么躺了很久,确认自己已完全从这漫长的梦中醒来。又是十一点过,屏幕上有一堆未读的消息。我全部划掉,直接拨通电话/
“干什么去了又不回消息!”
“我想到很重要的事。”
“哦?”
“我的‘季鸟儿’,也许是一条大鱼。”
“……你小子,偷偷写东西是吧!等着,我马上过来!”
雨生啊雨生,你要游到更远的地方。放下电话,窗外雨声依旧。朋友或许还有很久才会到,于是我闭眼靠在椅背上,构思起一个故事。